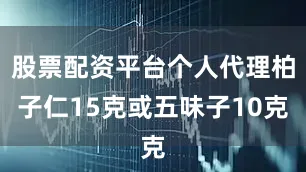“小时候,地理老师要我们在中国版图上画出行政管辖区的形态图,费煞脑筋。不要说画出原样,就是让你迅速指辨,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但是,要你指认台湾,所有人都可以不假思索地指向东南方位的一个小点,图形虽不大,却非常瞩目。”
这段出自画家周矩敏先生的文字,像说我的经历,初中地理期中考试,我没在地图上找到苏州,只找到台湾和新疆,台湾孤选一点,而往大片空白处划去,“新疆”,蒙对了。
没想到周矩敏先生文字也有他的画那么有趣。有趣是重要的,在我看来,有趣是一个艺术家的天赋。谢赫“六法”,第一法“气韵生动”,有趣就是“气韵”,大概率非学而知之,往往生而有之。学问属于“骨法用笔”,交游属于“经营位置”……比赛第三,友谊第二,有趣第一。
周矩敏先生人也有趣,和他聊天,他会讲一只又一只故事,而这些故事,都与他有关,听完后,却一点也不觉得他自恋。
展开剩余83%有一天,我在平江路上邂逅法师,就站路旁说话,几位女士经过,向法师合十,法师正和我说话,没及时还礼,脸色突然微红。我喜欢上这个法师了,他有种天真。
我们已经不会脸红了。
周矩敏先生还会脸红。他讲着讲着,有时脸色突然微红,他有种天真。
说到底,周矩敏先生毕竟书生。
“百无一用是书生”,周矩敏先生不是这样,他在现实之中,能力也强。
这是一个比喻:我总觉得周矩敏先生收藏不同类型的胶木唱片,随身携带唱机,遇到青春万岁,他在唱机里放上花腔女高音;遇到老气横秋,他在唱机里放上十八张半;遇到你,他在唱机里放上《团结就是力量》;遇到我,他在唱机里放上《国际歌》。周矩敏先生转换自如、自然,绝不拖泥带水。
他了不起的地方,别人这么做,我可能会觉得过于圆融,在周矩敏先生这里,你看到的只是质地纯粹。以致我不乏书生气地想起奥顿的两句诗:
而在他自己脆弱一身中,他必须
尽可能隐忍人类所有的委屈。
也就是说,他是做事的人,成事的人。每每与周矩敏先生相遇,我就十分惭愧,想起祖母指着我说,你啊你啊,受不了一点委屈,终将一事无成。
“尽可能隐忍人类所有的委屈”,在我看来,也是一个艺术家的天赋。
我与周矩敏先生没有单独相处过,见面时候,经常一大堆人,有喊他“老师”的,有喊他“先生”的,有喊他“周局”的,有喊他“周院”的,有喊他“矩敏”的……
周矩敏先生海纳百川,确实在苏州艺术家里呈现出独特的格局。
苏州艺术家中,两个人的文章写得好,一个周矩敏先生,一个黄海先生。黄海先生叼着烟斗,喊着“矩敏矩敏”,周矩敏先生“诺诺诺诺”,黄海先生像是院长,周矩敏先生像是副院长,这情景也只有在苏州洒脱之地才能看到。
“我祖籍浙江宁波。宁波人问鼎上海商界是赫赫有名的。”
周矩敏先生出生于上海,他们家是做钟表生意的——“亨得利钟表”。钟表是舶来品,是先进文化……这些祖上业绩,也是周矩敏先生的文化基因,“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文化氛围”……据说钟在当时有个名字:“自鸣钟”;二三十年代,名物带“自”的,都有一种巧夺天工:“自行车”,“自来水”,“自来火”,“自来熟”,哈哈哈,“自来熟”不是。
周矩敏先生的画中,天生“自来熟”,所以让人看着亲切,“风月叠叠,水波漪漪,菰雨生凉,春露侵衣。月至中天,人入九霄。一帘春梦,几度李花,可知君思,最忆江南。”
“冬至前夜,章太炎的关门弟子朱季海在苏州最繁华的观前街一墙之隔的一座民国旧宅里,隐逸六十多年后安然仙逝。浮世隐士就这样悄然无声地走了。社会依旧,没有任何浪花!1月26日 21:30”,读着周矩敏先生的微博,哀而不伤,怨而不怒,这类文字看似波澜不惊,实有波澜。所以周矩敏先生创作《先生》系列,仿佛入了应许之地。
“‘先生’叫得最贴切最顺耳的,应该数民国时期的文人。因为叫一声‘先生’,如鲁迅、胡适、蔡元培、王国维、陈寅恪等一系列文人大师们会在脑海中自然跃出。极具画面感的形象也油然而生:一身布衣坐在藤椅中,一支久燃未吸的烟被夹在熏得焦黄的手指间任由漫燃,直至烫到手指。另一手持饱蘸墨汁的毛笔,时而奋笔疾书,时而干舔砚边,滞凝不动。一摞涂涂抹抹的信笺堆中,悠悠飘出乌龙茶的馨香,混合着砚池的墨香,随着缕缕烟雾弥漫于书斋。”
历时四年,周矩敏先生为150位近现代知识分子画像,用一己之力建造了水墨名人馆。
当时《先生》画展,在章园,也就是章太炎故居,我正滞留北方,没有得见。但章园是常常路过的,青少年时期,我住通关坊七号,那里有座晚清戏台,现在也被拆除了。拆除的理由是这类戏台苏州很多,以致拆来拆去,终于凤毛麟角。早春之际,我几乎天天去章园看辛夷,通关坊与章园仅隔一条窄窄的锦帆路,那里有棵我以为的苏州最大辛夷,后来,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被锯掉了。原因我当然知道,只是不想说,可以吗?可以说说辛夷。辛夷,又名紫玉兰,又名紫木笔,还有一个较为冷僻的名字:“书空”。
一枝枝含苞待放的紫木笔硬乔乔戳进苍穹,好像东晋殷浩“被废,在信安,终日恒书空作字。扬州吏民寻义逐之,窃视……”,见《世说新语》。意思是殷浩被贬之后,他整天用手指在空中书写“咄咄怪事”这四个字,此乃“书空”来历。
我参观过周矩敏先生在苏州美术馆的大展,人物、花鸟、山水,他是无所不能,他的《上海》系列,尤其让我震撼。苏州能画这么大画的人,据我所知,独此一家,在这个系列里,观念,功夫与工夫,才情,要什么有什么,上帝对周矩敏先生真是很好,如果有上帝的话。
我对上海很是隔膜,在我看来,苏州和上海,像两个国家,苏州是英国,上海是美国,上海从苏州那里获取过早期营养,苏州从上海那里得到过未来回报。这个未来,不是说没有实现,这个未来是从早期角度的观望。本质上,它们一体两翼。我这个比喻,来源于沈嘉禄先生,有次参加莼鲈论坛,晚餐之际与沈先生同桌,沈先生说:上海的文化是有几大块构成的,优质部分来自苏州。这个话,由我苏州人转述,似乎不太妥当。其实我身上的地区性也暧昧得很,我姓顾,祖籍松江,但松江我从没去过,有人在朋友圈晒塔,让大家猜在什么地方,我一眼就认出在松江。有些事真不好说。一言以蔽之:上海是目前中国最优质的文化符号。
周矩敏先生画《上海》,是对现代文明的一次礼赞,礼赞的性质远远大于“追忆逝水年华”。所以周矩敏先生的纯粹,是以现代文明作底色的,这不但在苏州,就是在中国,也很难得。
那天,我在周矩敏先生的大幅画前,无端端觉得,他的许多画里,都有一座百年自鸣钟独立风中,在自己的如梦的时间长河,钟声“叮当”作响,银帆一般肃穆端庄,静悄悄地穿越市井的喧哗与骚动。
“叮”!这钟声恍若站在楼上看云的人。
“当”!正点。
发布于:江苏省海证金融配资,信钰证券,启恒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